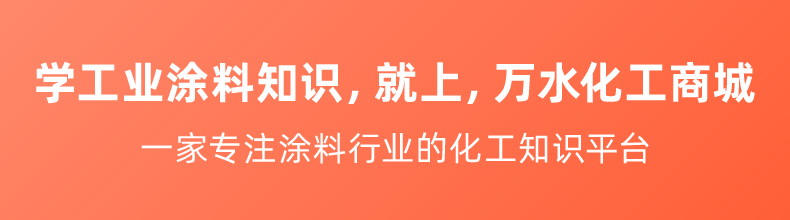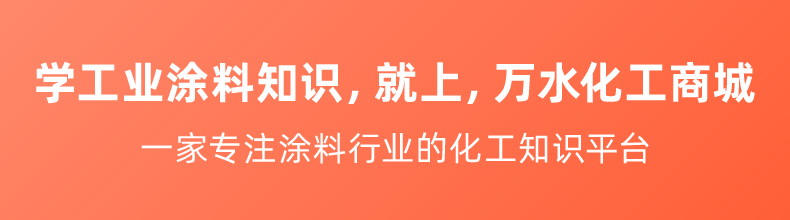
航空发动机冲蚀损伤及防护涂层研究进展
0 前言
作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航空发动机被誉为飞机的“心脏”,对其性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随着第四代航空发动机的研发与应用,其各项性能指标均显著提高,服役条件也更为严苛,冲蚀、磨损、氧化和腐蚀等各种因素会影响其耐用性[1]。航空业的发展伊始,就观察到在飞行过程中由雨水[2]、沙子[3]、火山灰[4]或其他冲蚀物对飞机造成的严重冲蚀作用。随着飞行时间的积累,这些损伤不仅会降低发动机部件的性能,还会导致更高的燃油消耗、发动机运行温度与涡轮入口温度,加速航空发动机部件的老化。同时,老化的部件也会加速发动机性能退化的速度,从而减少发动机整体使用寿命[5]。
本文从航空发动机的冲蚀形式、涂层防护以及测试体系三个方面介绍,旨在为航空发动机先进抗冲蚀涂层的发展提供更多理论基础和设计思路,并对抗冲蚀涂层的研究现状和应用进行总结。
1 航空发动机主要冲蚀损伤形式
航空发动机的冲蚀损伤,一般是指发动机部件材料表面和冲击流体之间的机械相互作用,使得材料表面逐渐发生损耗的现象[6]。当飞机飞越大气层时,发动机前向表面可能会受到不同颗粒物或飞行物的影响,尤其是固体颗粒和水滴直接或协同作用会对发动机部件产生冲蚀损伤,缩短部件的寿命周期,这些损伤包括:风扇/压气机叶片的冲蚀磨损、叶片冷却孔的堵塞、涡轮进口导叶上的灰尘沉积、燃料系统的老化和燃料喷嘴上碳基物质的沉积等[7]。由于服役环境、材料属性与空间位置的差异,航空发动机冷端与热端部件的冲蚀损伤形式存在较大的差异,航空发动机冷、热端部件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 涡扇发动机的横截面示意图[1]
Fig.1 Schematic cross-section of a turbofan aircraft engine [1]
1.1 航空发动机冷端部件
航空发动机的冷端部件通常在低于600℃的温度下运行,包括风扇叶片、压气机叶片和低压涡轮等[1]。发动机在服役过程中,易受到高速固体硬质颗粒或高速液滴的冲击造成冲蚀损伤。
1.1.1 固体颗粒冲蚀
固体颗粒冲蚀(SPE)是指拥有一定速度和尺度的固体颗粒在经过材料表面时,对材料表面造成的损伤现象[8]。影响固体颗粒冲蚀损伤因素包括颗粒尺寸、颗粒速度、冲蚀角度、冲蚀时间、环境温度、被冲蚀材料力学性能和材料显微结构等[9]。STACHOWIAK等[10]总结了不同速度固体粒子以不同冲蚀角度撞击不同材质固体时的失效模式,其中包括磨损、疲劳、塑性变形、断裂等。
对发动机造成冲蚀损伤的硬质颗粒主要为火山灰和砂粒。火山喷发可以将大量固体和气体物质喷射到大气中,并跟随大气现象移动到高空并扩散两年以上[4]。火山灰主要由坚硬、锋利的岩石碎片组成,同时常包含有硫化物或气溶胶,甚至在高海拔地区夹杂着冰晶和静电荷,对于塑料、玻璃和金属均可造成冲蚀损伤[7]。而航空飞行器,如军用战斗机或运输机等在高砂尘环境服役时,发动机的进气过滤器无法完全消除空气中的悬浮颗粒,如图2所示,砂尘将随高速气流吸入发动机内部,并使风扇、压气机叶片、轴流式涡轮叶片等受到冲蚀作用,导致工作效率的损失[11-13],目前,固体颗粒冲蚀损伤已成为航空发动机服役过程中最常见的损坏类型之一。
针对受固体颗粒冲蚀影响较大的压气机叶片,相关学者在大量试验积累以及经验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以下理论。
(1)磨损和二次冲蚀。HE、BOUSSER等[14-15] 认为,在高速气流夹裹硬质颗粒与固体表面发生冲撞并造成破坏的动态过程中,受冲击表面发生变形,颗粒动能通过塑性变形、断裂、升温、相变等多种机制部分或全部耗散。一般来说,对于塑性材料,发生小角度冲蚀时,主要的破坏模式为微切削,对于脆性材料,冲蚀角度较大时容易受到破坏,失效模式为弹塑性变形引起的表层剥落[16]。如图3所示,硬质颗粒在最初的冲击作用下发生回弹或发生破碎,粒度和冲击速度足够的破碎颗粒再次冲击固体表面,造成二次冲蚀。
(2)高应变率冲击。HE、VOGEL等[14-17]研究发现,航空发动机压气机叶片处于高速旋转状态,硬质颗粒以超过音速的相对速度高速冲击叶片,引起较高的应变,对叶片造成特殊破坏效果。而作用在颗粒上的叶片动能足够大,可以将颗粒或撞击产生的破碎颗粒由风扇核心流分离输送入旁路流,对叶片造成额外损伤。由于颗粒-叶片的相互作用以及颗粒破碎是高度复杂的过程,目前缺乏更进一步的解释。
图2 砂尘环境的发动机[14]
Fig.2 Engine exposed to sand [14]
图3 二次冲蚀过程图[14]
Fig.3 Diagram of secondary erosion process [14]
(3)冲击疲劳。HE、LI[14-18]等认为,硬质颗粒反复冲击固体表面造成应力集中,产生微裂纹或微损伤作为疲劳源,疲劳裂纹扩展造成固体表面宏观损伤[19]。
固体颗粒的冲蚀行为是复杂动态过程,受颗粒运动轨迹、冲蚀角度、固体表面应力状态、微观变形等众多因素影响,实际冲蚀理论分析难以全面考虑以上各项因素。因此,冲蚀模型的建立存在一定的适用局限与片面性,准确建立固体颗粒冲蚀理论模型仍是该研究的难点。
1.1.2 液滴冲蚀
雨水冲蚀或液滴冲蚀(WDE)一般定义为液滴连续撞击导致发动机部件表面材料逐渐流失的损伤行为[2]。当飞机在潮湿跑道起飞降落、穿过云层或者暴雨时,高速气流吸入液滴并撞击进气口处部件造成强烈的冲蚀损伤[20],如叶片会受到液滴高速 (300~400m/s)撞击产生表面损伤,改变前缘轮廓和表面粗糙度,严重影响气动性能,造成推力损失[21],增加颤振风险,增加燃油消耗并缩短叶片使用寿命,最终导致发动机效率下降[22]。此外,液滴也会加速固体颗粒对于航发叶片的冲蚀损伤。图4所示为雨水冲蚀损伤的叶片前缘。
图4 风扇叶片前缘的雨水冲蚀损伤[23]
Fig.4 Rain erosion damage ex-service turbofan blade[ 23]
BURSON、MA、FIELD等[21-24]分析总结了由高速液滴持续撞击风扇叶片等固体表面引起的冲蚀过程。
(1)直接变形。如图5所示,与固体表面高速撞击的瞬间,液滴快速膨胀形成压缩液体区域产生瞬时高压力,冲击表面发生局部塑性变形形成大量小的凹陷[25],或者产生拉伸破坏导致表面和亚表面损伤[26]。
(2)应力波。高压压缩液体产生压缩、剪切应力波并通过固体传播,与材料内部结构相互作用,到达微结构边界反射并持续作用,产生可导致进一步损伤的拉伸载荷区域[27]。
(3)高速横向射流。压缩液体沿液固边缘径向流动,产生十倍于撞击速度的高速横向射流,并与不规则的固体表面相互作用,产生剪切应力导致局部变形和亚微米级缺陷[25],聚结的微缺陷形成冲蚀坑。
图5 液滴与固体表面撞击的瞬间[24]
Fig.5 Initial stage of impact between a water drop and a solid target [24]
(4)液压穿透。液滴撞击固体表面产生冲蚀坑或微裂纹导致应力集中,持续作用下裂纹继续从冲蚀坑的侧壁和底部扩展,使亚微米级裂纹扩展到几毫米,引起固体表面几何形状进一步变化并导致承受冲击加剧,再次加速裂纹扩展直至产生宏观失效[22]。但由于现有液滴冲蚀机理模型普遍存在主观假设,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研究基本限于简化条件和样品的实验室测试[27],所提出的模型缺乏验证。因此,目前为止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或冲蚀模型可适用于实际的液滴冲蚀情况。
1.2 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
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包括燃烧室、高压涡轮、尾喷管等[28],主要由单晶镍基高温合金、钴基高温合金、陶瓷基复合材料及热障涂层等构成,在严苛的服役环境下受到复杂的冲蚀损伤,主要为高温颗粒冲蚀及高温多相流冲蚀。为了提高效率和推重比,航空发动机的工作温度自1960年来以每年近15K的速度快速上升。发动机热端部件使用的单晶镍基和钴基高温合金的最高使用温度被限制在1 100℃ 左右[1],为提高航空发动机燃油效率、获得更高的工作温度、改进性能并延长发动机部件寿命,发动机高温区域使用的材料存在严格要求[29]。为进一步提高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涡轮叶片等热端部件的抗高温能力[30],陶瓷基复合材料(CMC)是高温合金可行的替代品[31],且SiC/SiC部件已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和涡轮机(CFMLEAP发动机)的热端部件[32]。CFM公司在LEAP-X发动机的排气管道和喷嘴中使用了Al2O3/Al2O3 复合材料[33]。日本IHI公司大力开发用于飞机发动机的CMC部件,以实现性能改进和减轻重量[34]。同时,为了实现航空发动机的高能量转换效率,涡轮机需要有极高的入口温度[35],而热障涂层(TBC)的应用有效地实现了需求。PADTURE等[36]研究发现,使用厚度为100~500 μm的涂层配合内部的冷却系统,可显著降低热端部件100~300℃的表面温度,这使得现代发动机能够在高于高温合金熔化温度(~1 300 °C)的服役温度下运行,在减少冷却空气流量并提高燃气温度、发动机推力和效率[37]的同时可提升整体使用寿命。目前使用范围较广的热障涂层主要由电子束物理气相沉积(EB-PVD)、大气等离子喷涂(APS) 两种,其几何结构包括:耐热陶瓷面层(TC)、粘结层(BC)和高温合金基材[38],其中EB-PVD技术制备的热障涂层有更好的抗冲蚀能力[39]。
1.2.1 高温....
该文章只显示3分之一,如想阅读到这篇文章的完整内容,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打开我们的万水化工商城小程序,在首页“知识中心”栏目搜索文章标题继续进行阅读。万水化工商城收集100万+篇精细化工知识文章,旨在为您深入的了解行业知识和化工应用技巧。